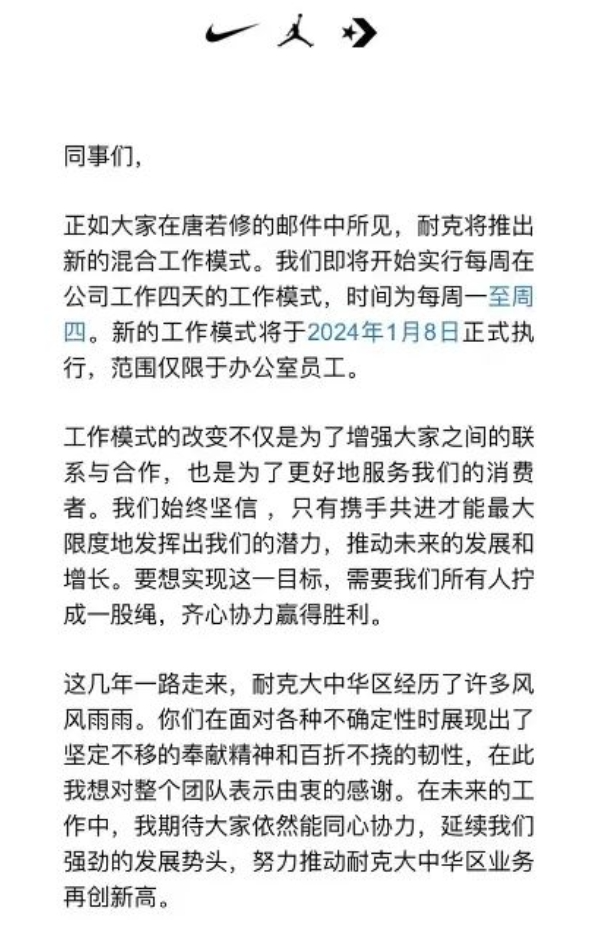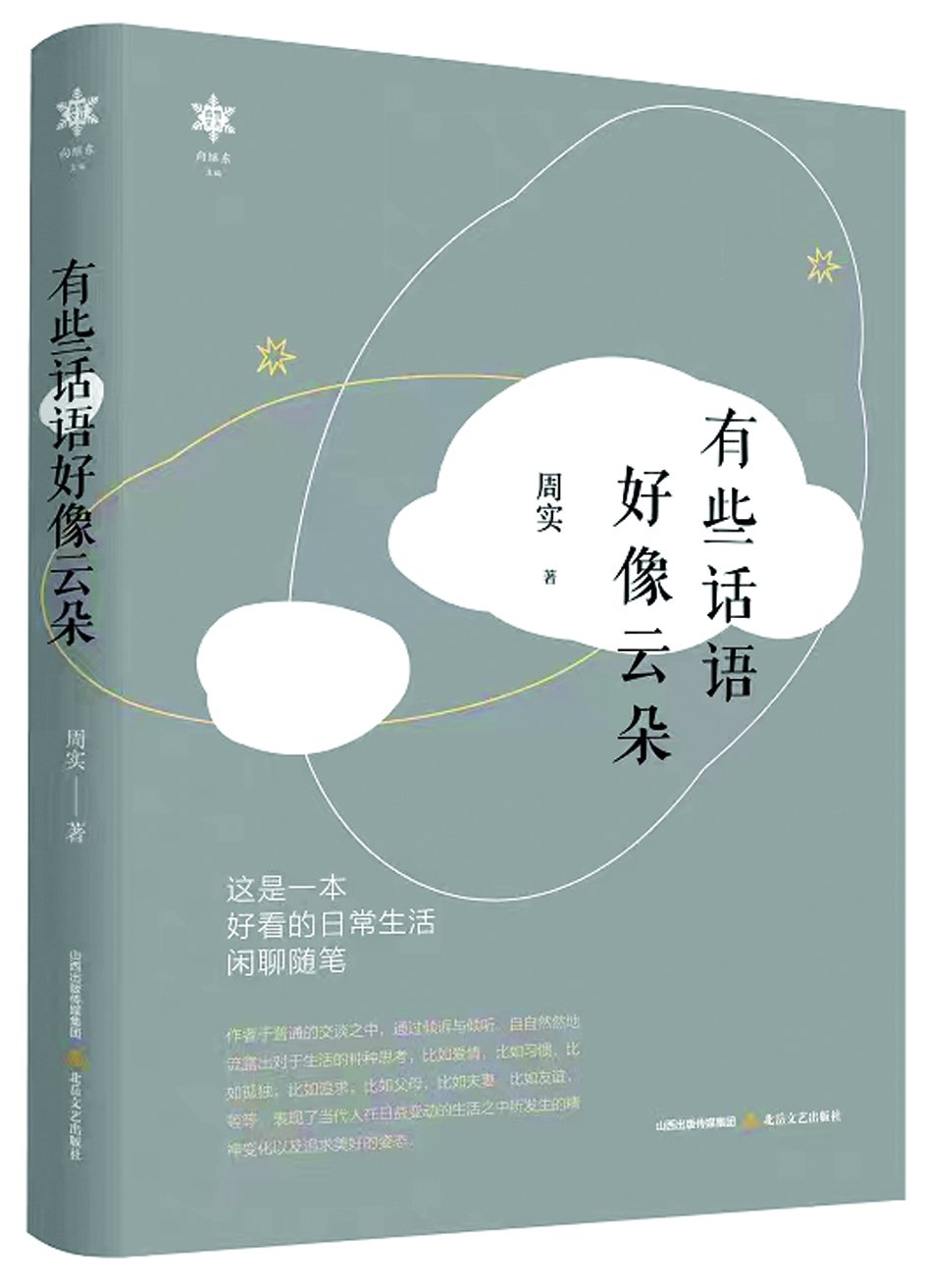“影院”一群视障者的“天堂电影院”
今天,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红星新闻的一群视障者的“天堂电影院”,如果您对一群视障者的“天堂电影院”感兴趣,请往下看。
轰隆隆的油门声中,一辆白色汽车全速前进,腾空飞出冲破天际。
荧屏前的人也跟着紧张起来,紧握双拳,汗珠不断从额头冒出。身体前倾着,头略微侧向一旁,想听得再清楚些。
解说员紧盯银幕,讲述着画面的流变。此刻每个人脑海中情形不同,但都一样屏气凝神,光映在他们脸上,扫过低垂的双眼。
5月9日,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,成都青芒影院放映厅里,42位视障者正在“观看”电影《人生路不熟》。
 ▲青芒影院为成都地区的视障朋友们带来《人生路不熟》电影,并有专业播音员进行无障碍解说。
▲青芒影院为成都地区的视障朋友们带来《人生路不熟》电影,并有专业播音员进行无障碍解说。一场特殊的放映
“奢华又高档,我们坐在枣红色的座位里,两边墙壁漆成翠绿,灯沿着台阶上升。”
李传立的想象中,这就是他看电影的地方。蓝本是童年时的乡镇影院,水磨石地面被踩得又滑又亮。青光眼夺去他的视力前,这是他对影院最后的记忆。
记忆中还有年轻的父母,为了保住儿子的眼睛变卖家产、整日奔波。直到挖了眼球,安上义眼,他大概想明白了:所谓治病就是有钱没钱,到头来都是倾尽所有。他不想再出门,此后三十年,他依赖脑中储存的形状和色彩,拼凑出身边的人和世界。
为了买一斤鸡蛋,他宁可绕到很远的小店,那里有熟悉的老板。“至少不会对我指指点点。是啊,我是能感觉到的。”
走到影院里的这一刻,他却没有这样的顾虑。放映前一个小时,老朋友们陆陆续续赶来,有的拄着盲杖,有的扶着志愿者的手臂,竖着耳朵寻找同伴的声音。“你来啦!”他们一把拉住对方的手,脸上绽放出笑容。
电影解说员曹雪菲提前半小时进入放映厅做准备,一盏台灯、一个话筒、一份40多页的剧本,他和搭档将交替讲述剧情。看着观众一边笑谈一边携手走进来,他觉得这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。一月一次的放映,多么执着的盼头。
坐得满满当当的厅里,最后一盏灯熄灭了。随着曹雪菲的声音响起,嗡嗡的场内瞬间安静。“现在放映的是出品公司的片头,正片即将开始……”
在人物对白间歇,解说员手拿剧本,对着画面解说场景。观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表达而波动,或是锁眉,或者微笑,或是沉思。导盲犬电影《小Q》放映时,听着片中的盲人决定自杀,导盲犬冲过去撞开了主人,避免了一场车祸时,不少人掏出纸巾擦拭泪水。

2018年,曹雪菲第一次成为了解说员。视障者出行不易,有人坐几个小时的公交专程来听电影,他担心自己讲不好,辜负了他们的辛苦。正片结束,现场一片寂静,随后响起雷霆般的掌声。一位盲人拉住他:您讲得特别好,我们都爱听。什么时候再来给我们讲?
明眼人能够捕捉到大量隐藏信息,但是视障者的想象空间有限,因此旁白一定要准确、简练,既不能喧宾夺主盖过片中对话,也不能代入太多情绪影响观众判断,而要引导他们感受电影的情绪。在讲述消防员为救人牺牲时,曹雪菲加入了留白。沉默也是一种语言,仿佛一声轻不可闻的叹息。
曹雪菲曾经关掉所有的灯,把自己沉入那片黑暗里——一种强烈的恐惧扑面而来,就像孤身一人走在无边的原野。他想到了父亲,因为黄斑病变而视力衰退,总是一次次小心翼翼地问:在哪里啊?他不耐烦地回应道:不就在这儿吗?
在这种恐惧之中,他理解了父亲——视障者需要帮助,但更需要的是一种自尊心。因为他们也同样不明白为何有这样的命运。
电影结束了,许多人都怅然若失。“啊,这就完了?还有吗?”坐在座位上等啊等,等到片尾曲也放完,他们仍然是意犹未尽,扶着墙慢慢往外走。“这是哪个演的?”“哎,好看好看。下一次是什么时候?”
“我们也渴望交流”
散场的时候,黄丹差点找不到门,她抱歉地摸着手中的盲杖说,第一次用,还不太会。
以往观影都有丈夫或者女儿陪同,这次她要求独自前来,“总不能一直让家里人陪着。”她的眼睛湿润明亮,瞳孔黑白分明。“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人生的前20年,黄丹读了中专,在运输公司上班,视线却越来越暗沉,像一团浓雾弥漫开来。婚礼上,只能等丈夫的酒杯主动来碰她的酒杯。
女儿出生时,她仅残存一丝视力,隐隐记得女儿像爸爸,“又丑又乖。”女儿已经14岁,黄丹一直在心里描摹她的形象。与女儿聊天、逛书店、拥抱,所有的这些感受都一笔一画构成了女儿的样子。每当加入了新的记忆,她的形象就更跃动一点,更深刻一点。
“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,眼睛是不重要的。”回忆起20岁时为前途患得患失的自己,黄丹觉得,时间带来了最多的安慰,因为它证明了盲人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。人不是因为有眼睛,才值得被爱的。
为了和女儿找到更多共同话题,去年她第一次走进了青芒影院,看了女儿最爱的《奇迹·笨小孩》。解说提供了丰富的细节,让她对剧情的理解有十之八九。“如果没有旁白,构建一部电影只能靠自己的揣摩,许多逻辑都对不上。”
最重要的是,她能看到时下热映的院线电影,聚会时便有新鲜的谈资。“我们也很想与时俱进。”

年逾花甲的刘泽跃自称“资深盲人”,他自幼失明却生性乐观,“天生看不见,也就不必在乎。”即便如此,他只去固定的超市和理发店,因为这些店“安全、有人情味”,老板对人也尊敬。
“安全”,是他来到青芒影院的原因。“我们内心都很想融入社会,但是又担心不被接纳。如果体验感不好,就容易让人望而却步。”他觉得,给视障者讲电影的人很有激情,最重要的是,他们一定很善良。
刘泽跃爱玩手机,有人好奇盲人怎么用微信、怎么支付、怎么打车,他都乐于分享。在地铁上遇到帮助他的人,他也想跟人家摆龙门阵。“要是人家了解我们,就会知道残疾人也有情有义,也尝遍了人情冷暖。”
他说,其实我们也渴望交流。
以观影无障碍,促人心无障碍
一个正常视线的人走在街上,世界对他来说是广阔的。 一个视障者坐在屋子里,活在一股粘稠的、迟滞的气息中。
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在地铁、公园、菜市场里,与你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一位视障人士。
中国约有1700万视障群体,在全球排名第一,每80人中约有1人存在视觉障碍。视障划分为四级,全盲的人群很少,多数人眼前是一片晦暗不明的世界。
相对而言,视障人群的就业机会较少。黄丹失明后找不到工作,只好去学按摩。“盲人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?”“连锁按摩店的老板。”这是这个群体内部流传的一个笑话。
以特殊之名,这个群体被抹去了生命多元历程的可能,一些盲人减少了社交的场所和频率,只活跃于残障者的圈子。
从来如此,便对么?
帮助视障者走出“孤岛”,是青芒影院创立的初衷。这个成立于2016年的成都本土公益组织已经放映了156场电影,保持每月一次的频率。三位发起者都曾是媒体人,一直在思考如何以自身资源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
电影可以让人与社会同频共振,三人一拍即合:要做,就做最新大片!
在贺麟教育基金会的支持孵化下,青芒影院应运而生,2016年走进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,2018年进入普通影院。成都影视服务中心提供了资金等支持,多家影院以极低的价格提供场地。解说员团队、无障碍电影剧本创作团队、志愿者团队也日益壮大。
从事电影发行的唐雅丽是一名志愿者,她觉得电影的魅力在于,在有限的人生中看见更多的可能性,视障人群的需求更甚。在青芒影院,他们终于有勇气说:“我也喜欢看电影。”
走,去影院!在口口相传中,观众从寥寥几人到场场坐满。
“针对残障人士的活动大多由残联组织,社会力量也不可缺失。”发起人之一李众说,这不仅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,也将进一步促进两个群体互相了解。他第一次知道,视障观众中有电台播音员、钢琴调音师、淘宝客服,与自己的日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听说李众为盲人放电影,一些熟人的反应是惊讶、好奇。其实这十几年间,盲人电影院已经走向全国各地,许多人致力于在一片黑暗的世界里,为视障者建起一座安全温馨的梦工厂。
每月第二个星期的周二,是青芒影院放映的时间,黄丹期待在这一天出门。她想坦然地走到街上、平滑地融入人流、自由地与路人攀谈,她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
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张芷旖 摄影记者 陶轲
编辑 陈怡西
好了,关于一群视障者的“天堂电影院”就讲到这。
版权及免责声明: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,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“科技金融网”,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。凡转载文章,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,如有侵权,请联系我们删除。
相关文章
- “尔森”用心倾听大自然的神秘邀约
- “考生”硕士统考发布报名提醒 考生需及时自查,抓紧时间修改
- “合肥市”“柿柿如意,柿如破竹”…… 高三学子“花式解压”
- “肌肉”磁铁刺激疗法可“对齐”肌肉纤维
- “低价”第15个双11:电商巨头争夺“最低价”、取消预售、开放生态
- “犯罪嫌疑人”湖南新化砍伤一对夫妇的犯罪嫌疑人落网,4人涉嫌窝藏罪被批捕
- “中国移动”中移动市场详情:合作伙伴大会重要发言及发布、反诈、5G应用获奖
- “血液”简单的血液检查调整可使重症监护治疗更安全
- “南充市”落马公安局长收受财物1365万被判7年:悔称利欲熏心,“金钱大厦”瞬间倾覆一生毁灭
- “高粱”河南固始有执法人员带人偷高粱?当地回应:涉事人员为行政执法大队人员,正调查
- “票房”消失的海外大片
- “前任”《前任4》热映,助力于文文主演电影票房破30亿
- “平遥”王俊凯任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特约策展人,将与贾樟柯对谈
- “电影”国庆电影静悄悄
- “雪豹”《草木人间》《老枪》《雪豹》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
- “票房”科技之心,电影之爱,未来可期:科视放映机为您呈现
- “电影”成都秋日夜生活“新玩法”:到公园吹着晚风看坝坝电影
- “考试”77人角逐广东“医考” 首迎香港考生
- “多伦多”多伦多电影节领“特别贡献奖”,刘德华:努力奋斗,做到最好
- “周报”电资办:2023年8月28日-9月3日全国电影票房周报